|
|
一鍵注冊��,加入手機(jī)圈
您需要 登錄 才可以下載或查看���,沒有帳號�?立即注冊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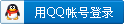 
x
--作者:謝文秀
碎片——一個右派妻子的回憶-1.jpg (57.13 KB, 下載次數(shù): 13)
下載附件
2022-9-23 09:22 上傳
邵燕祥和夫人謝文秀
回想起來真是幼稚,少年時總以為當(dāng)皺紋爬上眼角�����、雙鬢飛霜的時候,一個秋日的黃昏�,自己會翻看書里夾著的枯萎的花朵,感嘆如夢如煙的人生���,思念往昔的時光��,玩味淡淡的哀愁�。
青年����、中年一次又一次的震撼仿佛使我清醒一些,代替玫瑰色夢幻的是實(shí)實(shí)在在右派妻子的處境�。比起那些隨丈夫發(fā)配到邊疆的妻子,我的不幸自然也只是“淡淡的”����,甚至還算是“幸運(yùn)”的。從沒離開原先工作的新聞單位�,下放過幾次,也是名正言順的下放干部���,不算勞改���。
幸耶,不幸�����?只有自己心里明白����。從沒有挨餓受凍�����,更沒受過批斗,只是那些平平凡凡的日常生活�����,竟然也像強(qiáng)烈地震時甩出的糅著驚悸����、辛酸�����、無奈也還帶著一絲溫馨的碎片���,深深地嵌在腦海里,化不開�����,忘不了�。
羅網(wǎng)
即使在邵燕祥蒙受種種恥辱打入另冊���,我處境不佳的年代里,我也不能把一切不順心乃至倒霉的命運(yùn)全算在他的賬上。在一些人看來���,我并不是無辜的�。
有人說:瞧�����,這才是一對呢,都是右派言論�����。
這句話,我是1958年夏天在河北滄縣整風(fēng)時聽說的����。
我知道這意味著我也要被劃成右派了。
為什么�?
很簡單,是我又一次自投羅網(wǎng)����。
1958年初�,剛進(jìn)滄縣竇店村不久�,住在一戶下中農(nóng)家里,這家日子過得很艱難���,幾乎很少吃到純糧食�,我和他們六口人一起除了沒吃過觀音土以外���,各種代食品都嘗遍了��,黃菜盤子(一種野菜籽兒)���、棉籽餅、蘿卜條(甜蘿卜條�,即甜菜榨糖的下腳料)�����、糠,還有我叫不上名兒的能填肚子的各種野菜����、野草。戶主叫韓崇悌��,生產(chǎn)隊(duì)長�����,生活的重?fù)?dān)壓得他除了下地干活���,總是一言不發(fā)。瘦得皮包骨頭的大娘看著三個正在長身體的孫兒孫女缺乏營養(yǎng),忍不住數(shù)落了高級社的種種弊病,說還不如初級社。在一次團(tuán)支部會上����,我轉(zhuǎn)述了房東大娘的看法���,自以為是如實(shí)反映了下中農(nóng)的呼聲。
沒幾天團(tuán)支部又一次開會,是對我的批判會���。記得有一位黨員干部列席�,團(tuán)支部書記定調(diào)�����,指責(zé)我下放以來不好好改造思想���,還否定農(nóng)業(yè)合作化�,說什么高級社不如初級社,還有句話在心里沒說出來�����,就是初級社不如單干����。
盡管我在一年前剛在解放軍胸科醫(yī)院開過刀:因先天性動脈導(dǎo)管未閉動了結(jié)扎手術(shù)����,從小體質(zhì)又較弱�����,可在竇店干活毫不惜力�����,從未嫌苦怕累;我沒下過農(nóng)村�,更沒嘗過饑餓的滋味,看著農(nóng)民吃糠咽菜���,自己咬著牙也挺過來了��,沒有任何怨言�。但是沒用�,誰讓你說不合時宜的真話了����。這又一次埋下了禍根。
這到底算是第幾次,我也說不清。
參加工作以后�,我這個經(jīng)歷簡單(從沒參加過任何“反動黨團(tuán)”包括其外圍組織�����,也沒接觸過國民黨員和三青團(tuán)員)���,頭腦更簡單的學(xué)生,因?yàn)橹毖?���,一度居然成為肅反的審查對象���。
我在學(xué)校并不用功,可是少年時代學(xué)的知識多少在腦子里沉淀下一些印象。我記得中學(xué)的外國地理課本明明白白說:波羅的海三國立陶宛、拉脫維亞��、愛沙尼亞原先并不是蘇聯(lián)的領(lǐng)土,二次大戰(zhàn)爆發(fā)以后才并入蘇聯(lián)�����。不知什么鬼使神差��,我在某一次會上闡述了這一觀點(diǎn)��。我又喜歡跟一些同學(xué)打橋牌�����、聽音樂會�,偶爾還去喝咖啡�。這在一些人眼里�,無疑是堅(jiān)持資產(chǎn)階級生活方式,甚至還有反革命小集團(tuán)至少是落后小集團(tuán)之嫌��。
肅反運(yùn)動�,我不是明確的審查對象���,開了幾次會“幫助”我����,找我談話讓我揭發(fā)���。我揭發(fā)了別人�����,如巴金所說“跟在別人后面丟石塊”�����,為的是保護(hù)自己過關(guān)。
肅反的羅網(wǎng)��,我算是擦邊而過��,因?yàn)槲艺娴母锤锩鼪]有任何瓜葛�。當(dāng)然也因?yàn)楫?dāng)時主持電臺對內(nèi)部(即中央人民廣播電臺)工作的顧文華是位大事從不糊涂的領(lǐng)導(dǎo)��,他對我被支部列為肅反審查對象大概也覺得荒唐�。在他的領(lǐng)導(dǎo)下�����,對我的審查也就真成了走過場�����。
1957年鳴放時,我因忙于業(yè)務(wù)�����,沒在任何所謂煽風(fēng)點(diǎn)火的大字報(bào)上簽名,而燕祥��,起初也沒卷入����。后來風(fēng)向一變,我這個后知后覺的人對大禍臨頭沒絲毫預(yù)感�,非但不感到忐忑不安��,甚至還要對人民日報(bào)社論《這是為什么���?》說三道四��。同時表示不理解甚至憤慨的還有比我大幾歲�����、金陵女子大學(xué)畢業(yè)的李宜���。
燕祥被劃為右派��,我做夢也沒想到�,國慶節(jié)前開了黨支部擴(kuò)大會��,擴(kuò)大到團(tuán)支部��,當(dāng)然不包括我這個團(tuán)員����。我知道黨支部在“幫助”他,他不告訴我開會的內(nèi)容�,我也不問。那會兒的人�,包括我這個被視為典型資產(chǎn)階級小姐的青年,實(shí)際上組織紀(jì)律性極強(qiáng)�,從不打聽任何所謂黨內(nèi)機(jī)密。我大概太懵懵懂懂了��,不知道他已陷入天羅地網(wǎng)���,國慶假日,他留在宿舍寫材料���,我卻還有興致和同學(xué)一起去聽傅聰?shù)囊魳窌?br />
沒多久�����,對邵燕祥的斗爭不再保密��,黨支部書記何光在一個局黨組成員的支持下導(dǎo)演的一批又一批揭露他“罪行”的大字報(bào)出籠了����,一次又一次批判他“罪行”的會議召開了,何光還專門找我談話�����,讓我揭發(fā)邵的問題。我雖然心情矛盾�����、痛苦����,但是經(jīng)歷過政治運(yùn)動的我,知道自己辮子不少�,也擔(dān)心被揪出來,只能表態(tài)要劃清界限���,還列舉了我知道的他寄出而尚未發(fā)表的詩文�。
1957年我和李宜都被定為中右�,卻沒劃為右派。幾十年后才知道�,我這是沾了李宜的光。本來我和李宜的“右派材料”已經(jīng)在部分人中傳閱了�,只因李的姑母��、姑父是李伯釗(中央戲劇學(xué)院院長)��、楊尚昆(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),投鼠忌器�����,不看僧面看佛面�,支部要對李宜網(wǎng)開一面,我也跟著從網(wǎng)邊閃過去了�。
1958年滄縣整風(fēng)補(bǔ)課時,讓每個人寫大字報(bào)交心����,我竟然貼大字報(bào)說想不通邵是右派,還引經(jīng)據(jù)典:蘇聯(lián)的杜金采夫雖然寫了《不單是靠面包》受到批判���,但并未因此成為敵人云云�,還說如果邵是右派�����,那么��,我更是右派�����。急得一位下放在同村的好心人、電臺工業(yè)組的同事�,比我要明白幾千倍、幾萬倍的夏佛生恨鐵不成鋼地批評我:你根本不懂思想改造����。是的,我真不懂�。都到這個時候了,什么陽謀����、陰謀早已公之于眾,哪個知識分子不是噤若寒蟬���,我也是好不容易才逃出反右這一關(guān)�����,到補(bǔ)課了����,還要自投羅網(wǎng)��。
沒料到的是我又一次幸免于難。當(dāng)時不明就里���。后來得知,下放工作團(tuán)的領(lǐng)導(dǎo)核心中��,有三位老同志:重慶新華日報(bào)來的陳競寰�、膠東老區(qū)來的王治本和山西老區(qū)來的馬映泉(前二位已去世),力保我過了關(guān)���,理由是:已經(jīng)有一個右派了�����,別讓一家子都成右派�。真是菩薩心腸����。以后的日子里,他們多次見過我�,從不提這事���;燕祥和我從側(cè)面了解到當(dāng)年的實(shí)情���,也沒當(dāng)面感謝過他們。
我不是教徒���,但我真誠地祈求上帝:去世的二位上天堂,在人間的馬老健康長壽����!
門檻
從那以后,不論是邵燕祥���,還是我����,都曾多次虔誠地檢討���、認(rèn)錯,他總算在1959年秋被摘了“帽子”�,回電臺不宜留在編輯部�,調(diào)廣播文工團(tuán)。而我����,雖不適合當(dāng)記者�����,尤其不能搞工業(yè)報(bào)道(是怕我里通外國泄密,還是擔(dān)心我到重點(diǎn)工程搞破壞��?)����,從滄縣回電臺調(diào)離工業(yè)組��,到新聞組當(dāng)編輯。60年代初期����,周恩來、陳毅在廣州為知識分子包括“右派”說了點(diǎn)好話����,我的處境也有微妙的變化�����,一度居然把我調(diào)到記者組。沒過多久,“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”了���,我自然又調(diào)離記者組。我常說���,別看我這個小人物,我的工作調(diào)動還總是和大氣候緊緊關(guān)連著呢。
盡管對我的工作時有調(diào)整���,我也絕對沒有什么怨言��。看著那么多的右派家屬隨著丈夫去寧夏�����、內(nèi)蒙古落戶�,我除了感激,還有什么可說的����。
那些年�����,我真誠地感謝組織對他的挽救,感謝組織對我的幫助���。幾乎每次運(yùn)動����,每次年終小結(jié)�,都像祥林嫂說她的阿毛被狼叼走一樣,痛罵資產(chǎn)階級家庭�,檢討階級立場�����,又針對多年不馴服的毛病�,表示決心當(dāng)馴服工具���。
就像祥林嫂因?yàn)閮纱渭奕伺碌降鬲z被兩任丈夫扯成兩半捐了門檻贖罪一樣�����,燕祥和我在那些年里����,自我批判、自我否定�,悔過、認(rèn)錯�����、改造����,甚至緊跟。1959年反右傾運(yùn)動���,他剛從河北黃驊農(nóng)場調(diào)回北京����,根本鬧不清運(yùn)動的背景����,更不知道廬山會議批的是彭老總,反正《紅旗》雜志上批同路人����,也就跟著批。記得他寫的批判文章還被機(jī)關(guān)內(nèi)部的小報(bào)刊登了���,發(fā)表時沒有他的名字,只說是根據(jù)會議紀(jì)錄整理�����。60年代初期����,他又主動配合反修斗爭�����,把蘇聯(lián)作家柯切托夫維護(hù)斯大林的小說《葉爾紹夫兄弟》改編成話劇����,經(jīng)過孫維世等人指點(diǎn)修改后演出?���!罢庇遗伞眳⑴c的劇本,居然成了黨團(tuán)員內(nèi)部觀摩的話劇����,盡管他本人已被開除黨籍。真是極大的諷剌����!
1963年生的第二個孩子是個女兒���,起名叫甜甜。我們兩人已經(jīng)改造得絕沒有自己的意志�����,以為從此可以四平八穩(wěn)地過平常日子�,我們希望生活像蜜一樣甜����,哪還會去反黨、反對偉大領(lǐng)袖呢���!再說他也勞改過了��,我也沒少勞動���,應(yīng)該說已經(jīng)贖了罪?�?墒恰捌甙四暝賮硪淮巍?���!捐了門檻還是有罪�!
他那么樣的夾起尾巴做人�,從文藝界小整風(fēng)開始,又成了批判對象�����。只能說在劫難逃?�?!
門檻啊,門檻�����,如果是屠格涅夫筆下的《門檻》��,那是他心甘情愿的��。他從解放前參加地下黨外圍組織起�,就是抱著那樣的信念:
——呵,你想跨進(jìn)這門檻�,你知道等待你的是什么嗎?
——知道?��!媚锘卮鹫f
——知道寒冷����、饑餓�、憎恨、嘲笑�、蔑視、侮辱���、監(jiān)獄、疾病��,甚至死亡嗎��?
——知道��。
——知道你會跟人世隔絕�����,完全孤零零一個人嗎��?
——知道,我準(zhǔn)備好了……我愿意經(jīng)受一切苦難�,一切打擊。
——知道不僅要躲開敵人��,而且要拋棄親人���,離開朋友嗎�����?
——是的�,……都可以離開他們�����。
——好吧����。你情愿去犧牲嗎?
——是的����。
……
如今,門檻怎么成了魯迅筆下祥林嫂的了��?
而我,理所當(dāng)然要受株連�。
更大的風(fēng)浪終于來了。
冬日
三十二年前的冬天--1966年的冬天格外冷�。
我住一間朝北的小屋,暖氣似有若無�����,隔夜烤在暖氣上的襪子沒干�。我又給孩子們找出兩雙襪子,一雙有個小洞�,趕緊找針線縫上。
每星期一早上都是這么緊張����。不到五點(diǎn)半就起床,自己收拾停當(dāng)�����,給兩個孩子準(zhǔn)備好干凈衣服���,輕輕地叫醒兒子、女兒�。
鬧鬧、甜甜,乖�,起床,該上幼兒園了��。
兒子多少知道鐘點(diǎn)����,老大不情愿地問,媽媽��,幾點(diǎn)���?
六點(diǎn)都過了���,起來吧!
不�,幼兒園班車七點(diǎn)半才來呢,我再睡一會會兒�。
兒子說得不錯,班車離宿舍很近�,七點(diǎn)起床也不晚,可是……
鬧鬧���,乖起����,媽媽還要送妹妹上報(bào)國寺托兒所呢,晚了來不及����。聽媽媽話。
甜甜似醒未醒���,使勁揉眼睛���。
“妹妹都醒了,鬧鬧懂事�����,自個兒穿衣服�。我?guī)兔妹么����!?br />
全利索了�,又給孩子穿上大衣,戴上口罩���,到宿舍院兒里���,天還沒全亮�����。
六點(diǎn)四十五分�����,我把鬧鬧送到候班車地點(diǎn)--小馬路的南邊�����,那里挨著北京電臺的大門�,門前有一片空地�����,比較寬敞�����,即使有來往車輛也不至于碰著孩子��。他照例是第一個,也是半小時內(nèi)唯一的一個���。天還沒全亮��,馬路上靜悄悄的��,我替他把大衣領(lǐng)上的扣子扣緊����,圍巾圍緊��,一再叮嚀:“千萬別走遠(yuǎn)��,實(shí)在冷得不行����,就跺跺腳。鬧鬧勇敢��、能干����,不用媽媽送上班車,自個兒能行�����,是吧���!”兒子痛快地答應(yīng)了���,分手時還說了聲:“媽媽,再見�����!”
甜甜走得慢��,我只好抱著她往汽車站趕�。本來19路車直達(dá)報(bào)國寺,可那年修廣安門橋�,當(dāng)中要下來走一截。廣安門下車����,我實(shí)在抱不動了,拉著她的手過臨時搭的便橋��。橋周圍一片空曠�,撲面的大風(fēng)刮得我衣服仿佛被吹透了����。低頭看女兒��,穿的是哥哥的小大衣����,有點(diǎn)短,更擋不住凜冽的寒風(fēng)�����。我眼圈兒一紅����,責(zé)怪自己真不是好媽媽,怎么就沒想到給孩子準(zhǔn)備件厚大衣呢�,雖說幼兒園、托兒所都備早飯��,大冷天��,我怎么就不讓孩子吃一口再出門呢����!“甜甜�,這兒冷����,咱們快走�����,過橋上車就好了��?!彼o緊拉著我手,依偎著我的身子�,盡可能趕上我的腳步。一邊走一邊又怯怯地重復(fù)了多次的要求:“媽媽����,星期六早點(diǎn)兒接我,每次你來���,小朋友都走光了���。”女兒的要求不高,可是我沒法答應(yīng)���,又不忍心拒絕�,只好拐了一個彎:“你看�����,每星期六�����,媽媽總是顧著接你�;哥哥坐班車回宿舍,都是鄰居阿姨����、叔叔幫著接,媽媽對你好嗎����?”“好!”“對�,甜甜也好。好孩子�����,媽媽晚接也不鬧,是嗎���?”她點(diǎn)點(diǎn)頭�����。
從托兒所回來的路上,才又想起兒子��。我安慰自己��,班車會按時來的�����,他不會老在冷風(fēng)里獨(dú)自站著�����,也許還能遇上熟悉的叔叔阿姨����,跟他說說話,把他送上車。再說他也習(xí)慣了�����,將近半年都是這么過來的�����。有個經(jīng)常送孩子上班車的好心人告訴我�����,每次車一起動����,人家小孩兒總是擠在靠窗口的地方吱吱喳喳向爸爸、媽媽招手再見����,而他,一個孱弱白皙的小男孩兒���,安靜地坐在那兒�,一動不動���。
是的��,小時候有名的鬧鬧�����,現(xiàn)在仿佛變得特別乖�。我不也是么,都說我個性強(qiáng)���,如今不也得比誰都知趣�。
八點(diǎn)差五分���,我準(zhǔn)時到辦公室。
離婚
沒人硬性規(guī)定我每天必須按時上班���,是我給自己立下的規(guī)矩�。
倒也不僅僅因?yàn)槲母锏娘L(fēng)暴��,從小受的教育就是要遵時���,守信用�����。工作以后也習(xí)慣了按時上下班��。又何況如今����!
別人家里有事能晚會兒來,早點(diǎn)走����,我不能,誰讓我丈夫是專政對象����,進(jìn)了政訓(xùn)隊(duì)呢。據(jù)說已內(nèi)定開除公職����,到湖南洞庭湖邊的農(nóng)場勞動改造。我無法改變命運(yùn)�����,但是我要靠自己加倍的努力���,表明我對革命事業(yè)忠誠�����,對革命工作絕對認(rèn)真負(fù)責(zé)����、一絲不茍,也許這樣能稍稍改善一下處境��。我一再表明����,準(zhǔn)備跟丈夫離婚,給兒子邵小哨改姓名�,叫謝立新。女兒1963年生下來就跟我姓�����,理由自然是男女平等��,不過下意識里也想過���,萬一再有風(fēng)浪��,非離婚不可�����,一雙兒女一人一個也好��。沒想到��,不幸而言中���。
幾天前,我已把母親留給我作紀(jì)念的幾樣首飾交到部門的文革領(lǐng)導(dǎo)小組�����;前不久父親在上海病故���,我為表示與資產(chǎn)階級家庭劃清界限����,只發(fā)了一個電報(bào)給頂門立戶的哥哥:請酌情辦喪事�����,我不返滬。
我還能干些什么呢���?唯一可表白我心跡的只有拼命工作��。記得1958年下放結(jié)束時����,不少右派妻子調(diào)到寧夏�,我卻如期回到電臺。一位被認(rèn)為原則性極強(qiáng)的女上級沅華善意地透露了緣由:“像你這樣努力的業(yè)務(wù)干部���,中央電臺還是需要的���。”其實(shí)這只是一種說法��,要不是廣播局的梅益等領(lǐng)導(dǎo)有意讓邵以后(當(dāng)時他還在黃驊農(nóng)場勞改)調(diào)回機(jī)關(guān)���,我再努力也徒然。不過�,聽了這話倒讓我多少明白一點(diǎn):我沒有任何優(yōu)越條件,出身不好��,愛人是右派,只有業(yè)務(wù)是我唯一的救命稻草���。
受或多或少的株連�����,我算是過來人��?���?蛇@回來勢不善��。兒子五歲多���,女兒才三歲���,還有頭幾年剛寡居的婆母。怎么辦��?
早在他被隔離前���,我們就商議好:孩子由我一個人管����,住機(jī)關(guān)宿舍。根據(jù)以往的經(jīng)歷��,我存有僥幸心理�,也許還能留在電臺工作;他回家跟老母親住��,周末假日孩子也不去���,最好讓孩子慢慢忘了他這個爸爸���。記得最早是由我提出的,他沒意見��。
聯(lián)想起1957年那個讓人揪心的日子���,我們結(jié)婚才半年多����,大難臨頭��,我還傻得全然不明事理,表示即使他沒工作我也要養(yǎng)活他����。這回����,可真應(yīng)了那句人們熟悉的話,“夫妻本是同林鳥����,大限來時兩分飛”。選擇“分飛”無非是覺得可以暫時保住自己和孩子不受沖擊����,至于能不能飛出去,能不能飛到一片安穩(wěn)的樹林�,誰能預(yù)料?“兩分飛”對我來說最大的代價是要忍受人們心頭的非議�����。那些年不管人們口頭上如何革命���,可善良的人心中總有是非����。我把他攆回家,還不讓孩子跟奶奶見面���,我還是為人妻�����、為人母的女人嗎����,簡直是沒情沒義的勢利小人�����??上胂雰蓚€年幼純真的孩子,我別無選擇�。宿舍院兒里,電臺第一個被揪出來的少兒部主任鄭佳���,除被抄家外�����,連宿舍的房門口也貼滿了勒令低頭認(rèn)罪的大字報(bào)���;我要不堅(jiān)決點(diǎn)兒�����,過不了幾天,我們住的宿舍也會遭到劫難�����,孩子脆弱的心靈怎能經(jīng)住這樣殘酷的折磨�!我從不期望領(lǐng)導(dǎo)表揚(yáng)我立場堅(jiān)定,只是怕驚嚇著孩子����。
分別時,我忍不住哭了���,什么也說不出來��。他沒流淚�,一再說讓我多保重�,“要想開點(diǎn)����,一個人一輩子什么日子都要過的”����。一個夏日的夜晚,他帶著簡單的衣物離開了機(jī)關(guān)宿舍�����。
那幾個月����,我跟他沒有一點(diǎn)點(diǎn)聯(lián)系。
沒人相信我會真離婚�。從延安來的老播音員齊越對他說,你們是假離婚吧��!
是真是假�����,我也說不清���。形勢一緊張����,我就覺得怕早晚得辦正式手續(xù),甚至考慮得十分具體:離婚大概得上居委會或是法院辦手續(xù)��,在那種場合��,我能昧著良心嚴(yán)詞厲語指責(zé)他如何如何反動��,表明堅(jiān)決離婚的決心么����?恐怕不能��,我擔(dān)心自己終究控制不住感情��,會流淚����,甚至泣不成聲。那樣的離婚徒然落話柄��,挨批判�,倒不如先拖延些時日再說,也許時間長了�����,疏遠(yuǎn)了,感情也就淡薄了�。
我真是這么想的,從沒告訴過任何人���,燕祥也不清楚���,直到今天。
后來批判資產(chǎn)階級反動路線����,他從政訓(xùn)隊(duì)出來,我也沒敢讓他公然回家�����,都說右派要到運(yùn)動后期處理����,誰知道會落個什么下場。1967年春節(jié)前��,鄰居兩夫妻帶著孩子回老家探親,孩子們平時在托兒所����,一個單元里日常就我一個人,他偶爾晚上悄悄地來�����,深夜或凌晨待院兒里基本沒人時再離開���,合法夫妻的“非法”活動隱秘而短暫���,連孩子都不知道爸爸來過。沒過多久�����,鄰居回來了����,我們又恢復(fù)兩不相干的生活��。
大概預(yù)計(jì)到新的一輪沖擊將波及到他�。在這期間,他給我?guī)磉^兩封信,原信早就銷毀��,大意是讓我放心�����,再大的委屈��、折磨��,他都不會自殺�。他永遠(yuǎn)記住魯迅先生的話:名列于該殺之林則可,懸梁服毒是不來的���。
果然�����,1968年春��,他又一次被揪出來���,說是妄圖翻案的右派。
離婚分手的事又在我心頭翻騰開了����。
我找誰商量呢���,想來想去,有一位老同事��,早在50年代后期就與右派丈夫離了婚����,之后一直帶著女兒過。我登門拜訪����,她不感意外,只是告訴我�����,如果不再結(jié)婚��,離婚后處境也改善不了多少��,怎么說也是孩子的生父���,自己的前夫;這個重要的社會關(guān)系不可能甩掉。本來我天真地以為離了婚孩子往后的日子會好過些���,少遭些白眼��,少受些歧視�,從未想到還要再找個什么人結(jié)婚��。既然如此���,我也只好還是老主意��,拖���,拖,拖……
后來���,受沖擊的人越來越多��,那么多反革命����、黑幫��、“5·16”、叛徒��、特務(wù)����,有時簡直像走馬燈,今天還是一派頭頭��,明天成了黑手�����;這會兒是革命干部��,過一陣又成了叛徒�����,他們或她們的家人大都照樣過日子��,我責(zé)怪自己干嘛那么驚慌失措��,自尋煩惱�����,還是得過且過吧�。
盡管我下過幾次決心,一刀兩斷�,劃清界限,最終還是齊越說得對:是一場假離婚�。
我從少年時就耳濡目染了那么些良心、情義等等價值觀念���,遇到思想不通強(qiáng)迫自己采取某一項(xiàng)行動時����,好像心靈無時無刻不受熬煎���,有時也想學(xué)著硬硬心腸�����,快刀斬亂麻��,不行�,心里發(fā)虛��。我大概命里注定��,一輩子也成不了翻手為云,覆手為雨�����,識時務(wù)的聰明人����。作為妻子,只能是劃不清界限的女人�����;作為編輯�����,我則是個只認(rèn)死理而不會“轉(zhuǎn)彎子”的迂者���。
要強(qiáng)
我自以為是個要強(qiáng)的人�����。
那一陣工作���、開會�、學(xué)習(xí)��,哪頭也不敢耽誤��。文革開始剛興背“老三篇”時����,我和同辦公室同年齡的張赫玲很快就把“老三篇”和林彪為《毛主席語錄》寫的“再版前言”背得滾瓜爛熟��,一半虔誠一半逞強(qiáng)�,還夾著幾分不得已。反正�,我這個注定每次運(yùn)動都“落后”(不說你反動就是十分客氣的了)的人其實(shí)是從來不甘也不敢”落后”的。
不管心情如何�����,在公開場合我不愿失態(tài)�。1957年我跟他同一個部門,批他的大會���、小會��,凡是讓我參加的�,我都不動聲色坐在一旁,聽著各種上綱上線的批判�����,瞥一眼各種人投來的目光:幸災(zāi)樂禍��,冷淡�����,更多的卻是同情�。這次運(yùn)動來勢更猛,下跪�����、剃陰陽頭這些至少在電臺前所未聞的侮辱人格的種種�����,他無一幸免�����。
那天早上,我一進(jìn)廣播局大門�,就感到異樣,幾個年輕人惡狠狠地嚷嚷�����,把黑幫梅益揪出來���!接著中央電臺有人呼應(yīng),把鄭佳揪出來��!又有人喊�����,把……我趕緊快步走到辦公室坐在桌前����,不管走廊里有什么動靜,我總是一聲不吭���,低頭編稿�����,盡力掩飾自己的不安�。我認(rèn)出門口的年輕人中有一位是廣播學(xué)院剛畢業(yè)不久的女學(xué)生,是對外部(國際電臺)的文藝編輯�,總還會有對內(nèi)部(中央電臺)的人參加,都是些誰呢��?事后聽說把黑幫頭發(fā)剃成陰陽頭的是60年代初復(fù)旦大學(xué)新聞系畢業(yè)的���,曾跟我在一個部門工作過��;那個特地找來剪刀的我還比較熟悉�����,是個極為幼稚的小錄音員��。應(yīng)該說在廣播局當(dāng)時的一幫風(fēng)云人物中��,他們絕對不算最壞��,可是偏偏我認(rèn)為人品還算過得去的人會有這樣的“革命行動”���,真是不可思議。事后想起來�,覺得運(yùn)動一來�,那種瘋狂�����,那種“斗����、斗、斗”的氛圍��,還有歷次運(yùn)動過后積極分子被提拔的實(shí)惠��,真是把人性中最最丑惡���、最最殘酷的那一部分充分調(diào)動出來了。這幾十年��,我還多次遇到那位復(fù)旦的低我好幾班的校友和那位錄音員���,我們相處很好�����,有時還能說些真心話�。誰也不提當(dāng)年那些個事。
那些年在公眾場合����,不管聽到什么,看到什么���,我總是裝作無動于衷的樣子�。委屈���、眼淚只能往肚里咽����。每天上班���,特地穿得整整齊齊��,個別極熟的朋友半真半假的說��,你啊��,越是日子不好過越穿得筆挺�。筆挺顯然是夸張�����,不過確實(shí)不愿給人以可憐兮兮的印象。
1967年女兒轉(zhuǎn)進(jìn)廣播局幼兒園����,周末、周一早上不用兵分兩路��,疲于奔命��,我感到輕松多了�。運(yùn)動一開始那種焦急、畏懼的情緒也稍有減輕���。
兩個孩子誕生時�,我們的經(jīng)濟(jì)情況可以�,高興時給孩子縫點(diǎn)衣服�����,偶爾回上海��,親人送���、自己買�,孩子穿得不算差。文革后����,孩子長高了,原先的衣服嫌短嫌小���,到商店看看���,不管大人孩子都是四個兜的中山裝,價錢又不便宜�。我想想,還是自己動手吧����。平時開夜車怕影響第二天工作,萬一犯困出了差錯���,可擔(dān)當(dāng)不起����。星期六晚上孩子們睡下后就是我做針線活的時間�����,縫紉機(jī)經(jīng)常踩到半夜兩三點(diǎn)。會縫紉的大姐也曾給孩子做幾件夾克衫寄來����。哥哥和二姐也沒忘了給我兩個孩子買幾件童裝。就這么著�����,兒子從小到成年沒穿過一件千篇一律的中山裝�。我還記得,女兒有一件淺藍(lán)色燈芯絨外套�,又短又小�,我把它改成一件后邊開的背心,還鑲了深藍(lán)的邊���,她穿了好幾年�����??赡苁?969年���,形勢稍許緩和一些��,上海的哥哥來京出差特地為女兒帶來了當(dāng)時最時興的小軍裝�����,女兒挺喜歡���,我始終沒讓她穿��,轉(zhuǎn)送出去了�����。鋪天蓋地的草綠色�����,我不只是看煩了�����,還有一種說不出的恐懼:得意揚(yáng)揚(yáng)自以為天生高人一頭的紅衛(wèi)兵�,抄家時用皮帶抽人的紅衛(wèi)兵���,成天繃著臉訓(xùn)斥人的軍宣隊(duì)���,哪個都穿著一身綠�。
以往節(jié)假日孩子都上奶奶家���,奶奶家去不成�����,我就設(shè)法帶他們上公園�����,讓他們也跟健全家庭的小朋友一樣���,有歡樂的童年。
文革開始一兩年��,我還參加節(jié)日報(bào)道或重大報(bào)道的最后復(fù)制合成工作��,外出采訪自然就免了��。復(fù)制合成時間性強(qiáng)���,容不得出一點(diǎn)差錯��,好在這些活我干了多年�����,并不怵�,麻煩的是晚上播出后還不算完�,必須等姚文元審定的新華社稿來以后,以欽定稿為準(zhǔn)修改�����。這樣��,白天干了一天��,晚上休息片刻又要接著工作����。改完還不能走,誰知道什么時候又來個改稿呢����,得到第二天清晨拿到《人民日報(bào)》大樣����,我才算完成任務(wù)���。
在機(jī)房時�,我盡可能鎮(zhèn)靜�����、細(xì)心����,動作敏捷,除了眼前的錄音帶��、文字稿�����,什么都不想�����。出了機(jī)房,有點(diǎn)空閑����,就要想這想那�����,想起那一雙沒人接的兒女�,該在幼兒園長老安伯伯家安睡了吧。老安伯伯是位老革命�����,文化水平不高�����,心眼兒好�����。每逢節(jié)假日誰家孩子沒人接���,他理所當(dāng)然地把孩子安頓在自家�����。我那一兒一女是老安家節(jié)假日的?���?汀V钡浆F(xiàn)在�,我還清晰地回想起他微微彎曲的身軀,帶著濃重南方口音的普通話��。每次我從他家接回孩子一再表示謝意�,他和老伴只是輕輕地說,孩子挺好��,快走吧�����,帶孩子好好玩玩��。
是的���,那天我上幼兒園接孩子已經(jīng)是5月2日早上快八點(diǎn)了�����。第二天一早���,他們又該回幼兒園過集體生活�,這僅有的一天�����,不能委屈孩子��?��!白撸蹅兩媳焙9珗@去�!”兩個孩子一邊跳著蹦著,一邊搶著告訴我頭天夜晚怎樣在老安伯伯家的房頂上看天安門放花���。雖說連續(xù)工作了一天一夜���,看孩子們這么興奮,倒也不覺得困乏��?���!罢婧每?,媽媽�����,轟一下���,半邊天全亮了�,紫的����、黃的、銀色的����,比在奶奶家都看得清楚?����!薄澳銈冊趺瓷系姆?���?可要小心?�?��!”“老安伯伯家的大哥哥、大姐姐把我們弄上去的�。沒事的?��!?br />
國慶節(jié)夜晚看放花��,北京人得天獨(dú)厚的享受����、樂趣��,對我仿佛已經(jīng)陌生了�����。1956年的國慶�����,燕祥要寫一篇節(jié)日夜晚的特寫��,我陪他走在西長安街上���,望著星空一簇又一簇的焰火����,我們隨便談著���,他說起火樹銀花��,我忽然聯(lián)想到在上?����?催^的美國歌舞片《火樹銀花》�����,不過沒好意思說出口����,當(dāng)時他正真誠地幫助單純得近乎幼稚的我�,多讀蘇聯(lián)的革命題材的文藝作品,我怎能念念不忘少年時看的美國電影呢!我一直覺得他比我革命得多����,甚至認(rèn)為過于刻板,不會跳舞��、不會打橋牌����、不會……我做夢也沒想到,才一年時間�����,這個溫文爾雅的共產(chǎn)黨員被批成青面獠牙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敵人��。
唉���,越想越遠(yuǎn),想哪兒了���。
忘了哪一年�����,可能是1967年�����,六一兒童節(jié)正趕上星期日���,我們?nèi)似鹆藗€早兒����,到頤和園門口才七點(diǎn)��。清晨的公園空氣分外新鮮��,我?guī)е麄兊侨f壽山��,游昆明湖�����,照了幾張相��。兄妹倆有兩張單人相片后來放大了:在十七孔橋上���,哥哥的那張笑容有點(diǎn)尷尬�����,是硬逗出來的�,妹妹倒是抱緊了斜挎的軍用水壺,樂開了花�����。誰能猜到這是一對享受不到父愛的孩子�!
第二天上班,說起頭天的活動����,同事說我真是好興致,精氣神兒足�����。我也不知道那幾年哪來那么多用不完的勁����,年過三十的人,又不是多好的身體�����,不說是身心交瘁也是勉為其難����,居然頂下來了。人����,大概就靠繃著一股勁兒,松不得��,軟不得���。
鬧鐘
1968年初����,兒子回家到附近的育民小學(xué)上學(xué)���。
一直到臨開學(xué)我才把他從幼兒園接回來���。他所在班的孩子春節(jié)前就走空了,老師知道我家沒人照應(yīng)�����,就把他安排在小班,幫著小弟弟���、小妹妹系鞋帶�����,疊被子��,就這樣湊合了一個多月�����。
學(xué)校開學(xué)了����。好在學(xué)校離得近����,上學(xué)放學(xué)不用家長接送,放學(xué)后也沒什么功課�����,他總是在院子里和小伙伴玩一會兒����,等我下班。發(fā)愁的是晚上不好辦�,除了星期四、周末���、星期日����,機(jī)關(guān)里每晚都有活動:開會或者學(xué)習(xí)��。
我跟鬧鬧規(guī)定好:晚上媽媽不在家���,不去院兒里玩���,要按時睡覺。我特地買了個白色的小鬧鐘�����。每天下班后�,我匆匆忙忙胡亂做點(diǎn)晚餐,母子倆吃完���,替他洗臉洗腳����,然后往放在地上的搪瓷壺灌點(diǎn)兒開水(不敢讓孩子動熱水瓶,怕不小心燙傷��,兩個孩子直到十來歲���,都不習(xí)慣喝熱開水)���,然后把鬧鐘鈴撥到八點(diǎn),要求他鬧鈴一響���,就脫衣服上床�?��!耙呛ε?���,可以不關(guān)燈�。”
幾天下來��,同一單元的鄰居直夸鬧鬧乖,說鬧鈴一響�����,他準(zhǔn)忙著睡覺����。我也相信他守信用����,每晚回家,屋里燈亮著�,人卻睡得熟透了。
有一次�,不知道有什么緊急任務(wù),我沒能回家吃飯�����,也就不可能給他上鬧鐘��。鄰居高阿姨兩口子是廣播學(xué)院老師�,學(xué)校不上課,經(jīng)常在宿舍��,一看六點(diǎn)多了,我還沒回家��,就讓鬧鬧跟著她家吃了晚飯��。
到八點(diǎn)我還沒回家��,高阿姨提醒說�����,鬧鬧���,該睡了�。
“不�,我等媽媽?�!?br />
“八點(diǎn)了���,到睡覺時間了�����?����!?br />
“不��,我媽的鬧鈴還沒響呢��?�!?br />
“你媽今晚沒回來吃飯�,沒撥鬧鈴���,鬧鈴不會響�,別等了���?����!?br />
“不��,我等����。”
就這么大概等到快十點(diǎn)實(shí)在睜不開眼了���,才在鄰居的督促下胡亂洗了洗上床�����。
第二天早上�����,我叫醒他�,他還問呢��,媽媽�����,你昨天怎么沒給我上鬧鈴��?
我心疼地嗔怪他:“傻孩子���,以后別老等鬧鈴響�,媽媽工作忙回不來就聽阿姨的話?��!?br />
到秋天��,加強(qiáng)戰(zhàn)備的一號通令下來����,讓各家老小盡可能疏散�����,我想一家三口決不能再分開����,再說我也沒地方安排孩子��。共住一套房的鄰居把孩子送回江蘇老家�,走了;對門單元和中間單元的幾戶�����,有的請假去外地安排老小���,有的也是晚上開會學(xué)習(xí)��。到晚上整個四樓經(jīng)常只有鬧鬧一個人���。再不用什么鬧鐘��,吃完晚飯���,洗完,就讓他鉆被窩���,還一再囑咐���,誰叫門也不開。開始孩子不愿意��,說太早睡不著��,可想想一個人玩也沒意思��,也還有幾分害怕�����,最后終于同意。那一冬����,熟人看見都說鬧鬧又白又胖,其實(shí)沒別的法寶�,就是睡得多。
白鬧鐘是為兒子上學(xué)買的�����,按時擦鬧鐘也就成了他的專職�,很長時間鐘的外表顯得白凈、明亮���,可是機(jī)芯慢慢衰老了���,開始拿到鐘表店加點(diǎn)油,又滴答滴答走起來�,再后來鐘表店師傅說你這鐘該淘汰了���,加油也白搭�����。畢竟艱難時期跟我們做過伴����,我把鬧鐘放在五屜柜的玻璃門里,時不時地看它一眼�。可家里破舊東西實(shí)在太多�,終于戀戀不舍地把它扔了。那個五屜柜最終也處理了���,我還記得柜門上留著的印痕����。那會兒浴室兩家合用��,零七八碎的都放屋里���,他們個子矮����,我在五屜柜抽屜圓把手上掛兩條小毛巾�����,天長日久,水漬的痕跡再也抹不掉了����。
抹不掉的又何止是水漬!
師傅
我始終相信好人任何時候不會泯滅良知����,即使在瘋狂年代。
做夢也沒想到����,工宣隊(duì)的范師傅毅然決然做出決定,不讓我上郊區(qū)短期勞動�����。
從50年代以來�����,我是單位里理所當(dāng)然最需要改造的�����,1958年下放勞動��、1964年“四清”��,還有每年半個月的勞動�����,我都是不可缺少的勞動力��。
1968年秋天�����,我所在的部門要派一人到郊區(qū)勞動半個月���,支部書記鄒大昌通知我去�����。決定自然不是隨便做出的����,部門十幾個人���,年輕的單身漢就四五個���,有孩子的也都不是單親家庭����,只有我一個人帶兩個孩子�����。我清楚:這是有意出難題����。以往,我跟這位農(nóng)民出身的支部書記沒有任何齟齬���,文革開始從他揭露走資派的大字報(bào)中��,才揣摸出一些思路:領(lǐng)導(dǎo)沒讓他當(dāng)”官”����,就是打擊工農(nóng)干部���,可是我這么多年連個小組長也不是��,礙他什么事�;也許因?yàn)槲沂撬^業(yè)務(wù)骨干,客觀上得罪了他����。對了���,運(yùn)動開始作為部門文革領(lǐng)導(dǎo)小組的他整過張赫玲�����,一位少年參軍�����,后來調(diào)干上大學(xué)的女黨員���,只因?yàn)樗?dāng)《閱讀與欣賞》節(jié)目編輯時十分盡責(zé),落下的罪名是散布封資修大毒草���,為復(fù)辟資本主義作輿論準(zhǔn)備�����。運(yùn)動一開始��,張赫玲成了挨批的重點(diǎn)���,我為張打抱不平�����,當(dāng)然又得罪了他���。第一重“得罪”實(shí)非故意,第二重“得罪”�,是咎由自取,我怎么又忘乎所以仗義執(zhí)言了呢���,真是“改也難”���。既然如此,我也只能吞下苦果�����。
我籌劃了一下:在機(jī)關(guān)幼兒園全托的甜甜周末不接�����,請老安伯伯老兩口再辛苦一兩次;可上學(xué)的鬧鬧怎么辦���,三頓飯��、早晚全靠我一人照應(yīng)。作為爸爸的他��,一個被專政對象���,正在郊區(qū)農(nóng)村勞動���,當(dāng)然幫不上忙。我對支部書記說:“我可以去����,但是孩子只能住到崇文門內(nèi)奶奶家?����!币粋€不到八歲的孩子每天乘公共汽車上學(xué)���,還得過兩條馬路�����,我想��,他要是還有一點(diǎn)起碼的同情心�,會猶豫的。他不也有兒女嗎���,他難道就舍得自己的孩子冒這樣的風(fēng)險����?哪知�����,他還是執(zhí)意叫我去�。我有什么辦法,只好給孩子買月票���,準(zhǔn)備第二天開始“試運(yùn)轉(zhuǎn)”����。
剛來幾天的工宣隊(duì)那位稍胖的范師傅聽說這事,果斷制止了�。占領(lǐng)上層建筑的工人階級來臨,我做了足夠的思想準(zhǔn)備���,以為他們對我這個敵對階級的子女�、妻子不會有好臉色���,沒想到范師傅不僅長得慈眉善眼���,說話也很溫和����,全然不是想象中橫眉冷對的形象。他對我說了一句�����,讓這么小的孩子乘車來回過馬路�,太不安全,你別去了��。
簡單一句話�,拂去了我心頭的愁云����。師傅多好啊�。
我從學(xué)校畢業(yè)后,下鄉(xiāng)當(dāng)過農(nóng)民���,但從來沒進(jìn)工廠當(dāng)過工人���,也從沒有過師傅,而范師傅���,是我唯一的也是畢生難忘的師傅����。
我記得進(jìn)駐電臺的工宣隊(duì)是北京內(nèi)燃機(jī)廠派出的�����。近年來聽說這個大廠很不景氣�,比我年長十來歲的范師傅該早退休了,不知老范師傅身體可好�����,還記不記得當(dāng)年的事。我可是永遠(yuǎn)記住了他的音容笑貌:穿著一件淺灰的布棉大衣�,一口北京話,和顏悅色的����,多咱也沒聽他惡聲惡氣訓(xùn)人。
姥姥
也許真是天無絕人之路�����。班上有位工人師傅擋著不時飄來的凄風(fēng)冷雨����,鄰居姥姥的愛心又使我一進(jìn)單元門就感到人間的溫情。
姥姥姓高����,隨著女兒女婿住����。我們共住兩居室的單元房。姥姥來時就住廚房��,小夫妻帶著孩子住朝陽稍大的屋��,我住朝北的小屋。做飯的兩個蜂窩煤爐子就放在窄窄的過道里����。
姥姥是徐州人,勤快�����,大腳���,有把力氣����。一次我提著二三十斤白薯上四樓�����,正一步一步往上挪�,她見了一把拿去扛上了肩,噔噔一氣兒到四樓�����,弄得我慚愧不已����。她認(rèn)字不多���,可明白事理,熱誠�����,好學(xué)�,擅長做面食:搟餃子皮、餛飩皮���,蒸饅頭包子都是能手���。用鏊子烙又香又脆的薄餅,那明快麻利的動作看得我眼花繚亂�。烙薄餅不用煤氣爐,走廊里臨時用柴禾架起鏊子��,右邊放著面板�����,她邊搟面����,邊添柴,掌握火候�����,烙完一張���,用搟面棍輕輕一挑���,白白的餅就飛到了另一旁的笸籮里。她看我一個單身女人帶著一雙兒女����,勉強(qiáng)會燜飯炒菜,什么面食都不會做�����,想換換口味��,只能上食堂買�,這太浪費(fèi)。她教我干這干那。我跟她學(xué)會花兩毛錢買肉餡包餛飩�,秋天大白菜便宜,稍稍放點(diǎn)肉末或油渣蒸大餡包子���。連鬧鬧都學(xué)會了搟餃子皮��、餛飩皮��。高姥姥戴著花鏡��,跟我學(xué)會用縫紉機(jī)�����。
可能是1969年夏天的一個晚上��,天還沒全黑�,我正在班上開會�,忽然天氣驟變,一場大冰雹從天而降��。辦公室有孩子的無不惦念著�,尤其是汪玉芝和我。不久前汪的愛人所在的地質(zhì)學(xué)院外遷�����,她跟我一樣�����,一人帶著孩子��。隨著一陣陣雹子噼啪落地�����,樓里的玻璃窗被土豆大的冰雹砸得嘩啦啦散落到院兒里����。這么大響動絲毫改變不了會議的進(jìn)展,真是雷打不動����。我們雖然坐立不安揪著心也不敢請假。好不容易熬到散會����,一出門就覺得像深秋季節(jié),涼颼颼�����,地面上鋪滿了沒化開的大大小小的冰雹。汪和我匆匆返回宿舍��,才進(jìn)大院兒���,見到一個可憐巴巴的小孩踩著冰碴站那兒����,穿得單薄�,腳上是塑料涼鞋。小女孩見到汪玉芝�,委屈得都快哭了:“媽媽,媽媽���,我害怕�?!蔽翌櫜坏冒参窟@母女倆,趕緊回去��。往常這時候孩子們該睡了�����,這天他們和鄰居的小男孩兒在暖融融的屋里玩得正高興。鬧鬧畢竟大些�����,有條有理地告訴我����,朝南的大房間有塊玻璃碎了����,已經(jīng)用硬板紙擋上,咱家朝北的屋玻璃好好的�����。下冰雹的時候���,高姥姥擔(dān)心我和妹妹害怕����,讓我們先別睡��,先到大屋待著���。孩子們說:人多不害怕���。一場冰雹�,我的一兒一女安然度過�����,而汪玉芝的女兒從此落下了關(guān)節(jié)炎����。
不記得在這之前還是之后,部門安排人參加“拉練”�。當(dāng)時工宣隊(duì)已經(jīng)撤了,依舊是那位支部書記說了算����。不明白為什么,先后派兩人去�����,偏偏是汪與我�����。如果說我因言行不慎應(yīng)付出些代價,汪可是無辜的���。她的困難比我更多���,我畢竟有高姥姥可依靠。我知道姥姥挺辛苦����,除了淘氣的外孫����,又添了個小外孫女,我把食堂飯票��、零用錢都交給鬧鬧�����,讓他帶著妹妹到食堂吃飯�,按時睡覺,盡可能自力更生�。“拉練”回廣播局那一天我疲憊不堪����,想不到還沒進(jìn)機(jī)關(guān)大門��,遠(yuǎn)遠(yuǎn)就看見高姥姥領(lǐng)著兄妹倆笑盈盈在路口等我�����?�!霸趺粗牢医裉鞙?zhǔn)回來����?”孩子們回答:姥姥打聽來的��。一泓暖情���,不�,是親情��,涌上我的心頭�。
著名的單弦演員馬增惠也是我的患難之交。文革時他們兩夫婦受到不小沖擊���,政治處境比我好不到哪里去����,甚至更差,但是風(fēng)暴稍一平靜���,他們沒少幫我���。她們也是兩個孩子,大女兒謝藝是50年代生的����,比我兒女都大,兒子謝東年歲跟甜甜差不多�。鬧鬧上學(xué)后�����,甜甜還在廣播局幼兒園�����,班車一到����,我經(jīng)常不能準(zhǔn)時去�����,馬增惠騎車�����,前邊一個后邊一個�����,把我女兒一起接到她家���,謝藝先陪著玩。多少年了�����,孩子們還記得馬增惠阿姨�、謝凌霄伯伯,還有謝藝姐姐�。當(dāng)年的小頑皮謝東,從小就是一副好嗓子�,他成為歌星也是意料中的。
數(shù)不清多少好人關(guān)心過我們。廣播局共事多年的朋友大都不認(rèn)為燕祥會是什么敵人�����,由于種種可以理解的原因����,干部不好公然表示同情,而工人倒可以毫不含糊表明自己的態(tài)度�����。
那幾年�,他不少日子被隔離或挨批斗,但是鍋爐房的工人�����、清潔工��、司機(jī)經(jīng)常轉(zhuǎn)告他我和孩子的情況���。女兒猩紅熱后癤子長到耳朵眼兒里他知道,兒子上學(xué)功課不錯他也知道����。我的一動一靜無不在這些好心人的洞察之中��。直到現(xiàn)在偶爾在機(jī)關(guān)見面��,他們還惦著他:有的叫他詩人��,有的管他叫“干部”����,有的依舊稱他小邵�。
大約是他在干校的時候,我在電臺收到多年沒聯(lián)系的老同學(xué)來信����,是位女同學(xué),但筆跡剛勁��,全然不像出自女子之手����。我很奇怪,這封信被拆過�����。廣播局收發(fā)室的同志我大都熟悉,他們從不干這類事��,偶爾信件錯轉(zhuǎn)到聽眾來信組被拆�,退回時必注明。想來想去可能是有人出于對他的關(guān)懷�,唯恐我有“外心”。時過境遷之后���,提起這事��,他也這么看�,開玩笑說:“他們替我監(jiān)視你哪�����!”
孩子
朋友都知道�����,我從來不是愛讀詩的人���。1987年,復(fù)旦新聞系比我低一年的女同學(xué)孫惠群到我家來�,提起1953年歡送我們畢業(yè)時��,她朗誦的正是邵的詩《到遠(yuǎn)方去》����,而我��,真的�,好像沒一點(diǎn)印象。
我很少為好詩所感動�,大概缺少這方面的藝術(shù)細(xì)胞。但是��,有一次�����,我卻為他的一首不算出色的詩《童年》而動情���。
原諒我占一些篇幅����,稍稍引用這首詩:
太陽藏在大樓背后����,
媽媽還沒回來�����,
冷風(fēng)刮得小樹搖晃�����,
媽媽還沒回來���。
媽媽怎么還沒回來?
電線桿上路燈都亮了�����。
媽媽怎么還沒回來���?
地上的樹葉都嘩啦啦跑光了�����。
媽媽�,你快回來吧�,
妹妹的鼻子在玻璃窗上貼扁了。
媽媽���,你快回來吧
妹妹的肚子早就咕嚕咕嚕響了�����。
……
媽媽�,自從爸爸不再回家��,
我和妹妹多聽你的話�����;
媽媽�,你可別也不回家,
那讓我跟妹妹怎么辦哪����!
媽媽,回家來吧
我的肚子也餓得慌啦�。
媽媽,回家來吧����,
我把棉衣給妹妹披上啦。
……
媽媽���,媽媽�,妹妹老是哭,
不是妹妹不聽話����;
媽媽,不怪妹妹�����,不怪她�����,
我也是又餓又害怕����。
……
其實(shí),我從未告訴他我一個人帶領(lǐng)兩個孩子時的處境��。他大約也是憑想象�,猜測哥哥和妹妹盼望媽媽回家的心情。
讀著讀著�����,眼淚撲簌簌流了下來。
想起那些日子���,孩子上小學(xué)以后���,每次回到我那間十二平米的宿舍�����,孩子們都親熱的圍著我說這說那���。而我��,有時心情不好����,加上工作太忙��,只是像機(jī)器人一樣忙不迭地催他們快吃飯����,快洗臉,快做功課。只有快�����,才能讓我按時到班上開會或?qū)W習(xí)�;只有快,才能讓軍宣隊(duì)或支部書記找不出岔子(當(dāng)然�����,即使你開會再準(zhǔn)時�����,工作再努力�����,也擋不住他們在別的地方挑你的錯)�。等我晚上回到宿舍,他們都已經(jīng)安睡�����,第二天一早���,還是一個勁兒催���,快�����,快�����,快。
有一天晚上���,開完會就聽說要下達(dá)最新指示�����。那正是戰(zhàn)備的年代���,鄰居奉命疏散回江蘇,單元里沒人����,我急忙回家照看一下。回到宿舍���,輕輕叫醒兒子����,告訴說我得半夜才能回家��,這一折騰��,女兒醒了����,問我上哪兒,我說去游行��。
“那么晚了�����,媽媽別走����,我害怕!”女兒不讓我去����。一個單元里����,只剩他們兄妹倆�����。
兒子畢竟大兩歲�,沒吭聲。
“不怕�,媽媽不一會兒就回來?���!?br />
我明白自己是說謊��,誰知道什么時候能回�����?
我匆匆走出宿舍�。
等游行結(jié)束,已經(jīng)是下半夜了��。我輕輕推開房門,兄妹倆睡著了�����。妹妹緊緊拉著哥哥的手�。
第二天一早,鬧鬧像小大人一樣告訴我�����,媽媽�,你走了后妹妹老說,害怕�,害怕,我就讓她拉著我的手����,她就不鬧了。
當(dāng)時我的心即使不是鐵石心腸���,也已經(jīng)磨礪得粗糙而麻木了���。我只是淡淡地表揚(yáng)了一下鬧鬧,又忙著張羅他們加快動作�,趕緊上學(xué)�����。
相依為命的日子是悠長而平凡的�,一日三餐���,上班下班�����,開會學(xué)習(xí)��。
最讓我揪心的是孩子有病��。一個星期一的早晨���,甜甜直喊難受,試試體溫����,有點(diǎn)發(fā)燒�,我把鬧鬧送到候班車的地點(diǎn)后,急忙帶甜甜去兒童醫(yī)院����。經(jīng)驗(yàn)豐富的大夫很快診斷出是猩紅熱��,還指給我看她身上的小紅點(diǎn)點(diǎn)��,囑咐要隔離���,要多吃水果。怎么辦�?只能送甜甜上幼兒園,是的���,這是唯一的選擇�,那時的氣氛怎么可能請一個星期事假在家看孩子呢����!到幼兒園,我傾訴了自己的困難���,請求老師們幫助�����,他們一口承擔(dān)了看護(hù)孩子的責(zé)任��,極為負(fù)責(zé)的把鬧鬧也從班里叫出來�,因?yàn)樗鹛鸾佑|多,怕已受感染�����。我給老安的愛人也就是幼兒園的會計(jì)留下點(diǎn)錢�����,請她為孩子買點(diǎn)水果和營養(yǎng)品�����,又匆匆上班去了�����。第二天����,我抽中午時間去了幼兒園,兄妹倆住著兩間緊挨的平房����,里邊住著妹妹,外邊住著哥哥���。兩個孩子跟小朋友完全隔離���,相互之間也不直接接觸,但是兩人可以說說話�����,倒也不很寂寞�����。我真是感謝石碑幼兒園的老安和眾多的老師想得這么周到�����,安排得這么好����。我也感謝兩個孩子懂事、聽話�,直到甜甜的猩紅熱好利索了才回家。
文革初期的狂風(fēng)暴雨過去了。他已經(jīng)上了五七干校�,機(jī)關(guān)里漫長的斗批改、清理階級隊(duì)伍�、整黨、一打三反��,還有戰(zhàn)備等等對我來說都算不了什么風(fēng)浪��,我日復(fù)一日的等著��,等著����,等著孩子長大,等著他回來�,等著自己一天一天憔悴、衰老�����。
有一陣���,鄰居家的姥爺來了����,小小的單元里住著老少九口,連過道里也老有人���。
一個冬日,我白天參加體力勞動����,出了一身汗,晚上回到宿舍���,草草吃完飯就把走廊里做飯的小爐子搬到浴室洗澡����。那會兒�,宿舍的暖氣不熱,我們兩家洗澡都把燒旺了的爐子搬進(jìn)去�����,微微打開浴室的門�����。大家都很默契誰也不在過道走動�??蓜偟奖本┨接H的姥爺不知曉這些�,我也就緊緊關(guān)上浴室的門。洗到一半����,覺得胸悶、呼吸急促��,我知道讓煤氣熏了����,想往外跑,可是聽到老人仍在過道�����,只好掙扎著穿衣服�,勉強(qiáng)穿上我就沖出浴室往屋里跑,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�。蒙昽感到兒子叫我,媽媽���,媽媽怎么了���?原來我已經(jīng)躺在地上�,才意識到自己中了煤氣����,還好腦子沒糊涂,趕緊喊�,鬧鬧,開窗����!開窗��!鬧鬧開了窗����,一股冰冷的北風(fēng)刮了進(jìn)來,我這才慢慢爬起來����,讓鬧鬧扶著拽著上了床。
多少年過去�����,隨著時光的流逝���,孩子們對童年的記憶越來越模糊���,我也從沒向孩子們復(fù)述過當(dāng)年的情景�����,是我太理智����,太冷漠了����,還是往事不堪回首?我說不清�。
負(fù)疚
理學(xué)家認(rèn)為,對孩子期望越高孩子越可能成材���。
聽到或看到類似的報(bào)道�,我就有一種負(fù)疚之感�。
望子成龍是中國人比較普遍的心態(tài),而我們�,從孩子一生下來兩人就有種共識:別讓他們立大志向,太拔尖���。一輩子過平安乃至平庸的日子就好�。平安就是福。
過來人會理解我們���。他那些年如果不是太拔尖(反右派時的批判還大致圍繞所謂“罪行”上綱�����,當(dāng)右派后行政級別被降四級����,文革批判時仍有人念念不忘他十九歲時定為行政十四級��,可見十四級真是害苦了他)��,也許會幸免于當(dāng)右派的厄運(yùn)�����。而我�,也吃虧在于除了日常上班���、過日子�����,太喜歡想這想那��,不安分��,不馴服����,該裝糊涂的時候過于“清醒”,該隨大流表態(tài)轉(zhuǎn)彎子時又太執(zhí)著�。1957年我對《人民日報(bào)》發(fā)表《這是為什么?)的社論轉(zhuǎn)入反右派想不通��,并且公然說了出來:1958年整風(fēng)補(bǔ)課時�,我沒接受教訓(xùn),竟然貼大字報(bào)說想不通他是右派�。
在那個時代,現(xiàn)實(shí)生活也不可能讓我對下一代有什么過高的期望�。我是碰運(yùn)氣才上大學(xué)新聞系的,如果晚幾年考大學(xué)�,像我這樣的出身,充其量也只能念上師范大學(xué)�,還得各門功課優(yōu)秀。
我們的一兒一女生于60年代初,那是物質(zhì)生活雖然匱乏政治氣氛還不那么逼人的年代�����。我們大約過了兩三年平安日子��,也沒敢忘乎所以想培養(yǎng)孩子成名成家�����。沒多久���,文藝界開始小整風(fēng)���,他就陷入越織越密的羅網(wǎng),直到又一次滅頂之災(zāi)����。我更加牢記“歷史的經(jīng)驗(yàn)”��,千萬不要出人頭地��,千萬不要有不切合實(shí)際的夢想��。
文革前�,孩子由婆母照料��,我不知怎樣感謝善良的婆母給孩子的溫暖和教育��,她對任何人都和顏悅色���,不功利,對心疼的孫子孫女從不打罵�����,可孩子真聽她的��。跟她一樣����,兩個孩子從小就不虛榮,對人真誠���、熱心����。孩子們永遠(yuǎn)懷念慈祥的奶奶�,她去世已十余年,沒預(yù)先約定,孫兒孫女幾乎每年都去八寶山公墓看望她老人家�����。
那幾年�����,我好像工作忙得頭都抬不起來���,基本不管孩子����,記得婆母健在又心情好時�,半真半假地說我簡直像后媽。我笑笑���,反正是親的��,只不過顧不上就是了�����。
文革中,我無言地承擔(dān)起一切,承受了�,不等于能很好地?fù)?dān)起。
我很矛盾�����,鴻鵠之志實(shí)現(xiàn)不了固然痛苦�,完全讓孩子當(dāng)個隨遇而安的庸人又心不甘。
他們的學(xué)習(xí)�����,我?guī)缀醪挥貌傩?����,我?dān)心的是他們對渺茫的未來缺少足夠的準(zhǔn)備�。盡管70年代初就有工農(nóng)兵大學(xué)生,而在我家��,直到1977年����,上大學(xué)是我們絕對不敢提及的敏感話題。70年代中期����,“走后門”這一名詞家喻戶曉時���,我再三對孩子說:“別人家也許有這樣那樣的‘后門’,走后門上學(xué)����,走后門參軍,我們家只能靠自己���?�!笔强孔约簩W(xué)習(xí)深造����,還是靠自己成就一番事業(yè)��?我都沒法說���,我總不能說靠自己只為混碗平安飯吃吧���!反正我的所謂“教育”是含含糊糊、躲躲閃閃的�����。
從1966年夏天到1973年底他從干?��;鼐?,將近八年時間��,我在辛勞��、不安�、無望又有所期盼的等待中度過。我本是溫室長大的任性女子����,對他,對孩子�����,從沒耐心����,以往我對孩子發(fā)火時,婆母或他可以緩沖一下��,如今,全靠我一個人����。當(dāng)我情緒比較平穩(wěn)或理智時,格外心疼孩子��,耐心告誡他們學(xué)習(xí)要認(rèn)真��,做人要誠實(shí)�����。當(dāng)無法抵御的厄運(yùn)來臨時�,在眾人面前,我不得不冷靜�����、從容�;回到家里,不能也無法跟孩子說清自己的心境�,充塞在心頭的憂悶、委屈越積越多�����,越積越濃,終于有一天�����,爆發(fā)了�。
大約是1968年冬天��,鬧鬧剛上一年級����,有一天中午回家忘了戴帽子,我堅(jiān)持讓他返回學(xué)校取��,他說丟不了�����,下午還要上學(xué)���。半年前���,孩子的父親被軍管小組宣布為專政對象,這無疑相當(dāng)于最后定案��,那一陣我的心緒壞到極點(diǎn),終于控制不住了����。我可以找出許多理由說不全是跟孩子撒氣,是的�,那陣我確實(shí)想得很多:誰知道以后會把我們一家發(fā)落到哪兒,兒子將來會面臨什么樣的命運(yùn)��?從現(xiàn)在開始全家就要格外節(jié)儉……先是板著臉教訓(xùn)�,他很拗,不肯到學(xué)校取����,兩人相持不下,我動了手��,他還是不去�,氣憤之下抽了他一個耳光,他躺在地上號啕大哭�。鄰居高姥姥過來相勸,他終于委委屈屈地回學(xué)校取來了帽子�����。他走以后,我也暗暗哭泣��,我是怎么了����,難道孩子不去學(xué)校找帽子就犯下了彌天大罪,我委屈�,心里苦,怎能遷怒于他一個才七八歲的男孩兒�����。鬧鬧從小最受爺爺奶奶疼愛���,爺爺去世后,奶奶更是愛這個孫子�,燕祥也是好脾氣,說話從來都是細(xì)聲軟語��,只有我偶爾給過他“厲害”����,那也是雷聲大雨點(diǎn)小。這兩年���,我只含糊其詞地說爸爸不住這兒����,奶奶家也很少讓去,他也不多問��,更沒有為不讓上奶奶家哭鬧過���。多懂事的孩子��!我委屈�����,孩子難道不委屈�?
事后�,我有點(diǎn)后悔,可過于要強(qiáng)的個性又不允許我向年幼的兒子道歉�。后來他長大了,“再怎么說�����,我不該打你”���,我終于為不止一次的粗暴作了檢討�����。
如今��,鬧鬧����、甜甜都已長大成人。他們的童年���、少年雖說沒吃過苦����,但也確實(shí)長大在一個沒有父愛的家庭�,而我對孩子又沒有足夠的溫存和耐心��。這樣的家庭環(huán)境對孩子的情商發(fā)展終究有不利影響��。當(dāng)然�,我一直注意培養(yǎng)他們正直、誠實(shí)的好品德����。我很自信��,他們不會為虛榮所惑�,為錢財(cái)所害���,但是我又很迷茫��,我擔(dān)心�,過于執(zhí)著����、正直,會給他們帶來什么����?會不會為此付出代價?他們的人生道路還很漫長�,他們大概不會像我們一樣一次又一次地陷入階級斗爭的羅網(wǎng),但是他們能逃脫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其他羅網(wǎng)嗎���?我也真沒把握��。但愿他們能做個無愧于良知又不至于受到太多挫折的知識分子���,我也只能這么企盼�����。
記得80年代�,我讀過高紅十的一篇散文�����,說起她們那一代知青在農(nóng)村足足鍛煉了八年還多�����,她說��,有些人因?yàn)橛辛税四辏ù蠹s是指抗日戰(zhàn)爭)而受人尊敬��,并且得到種種優(yōu)厚待遇���,而我們最好的八年獻(xiàn)給了農(nóng)村,卻連工齡都不算……從1966年初夏到1973年底他從干?;鼐俏译y忘的八年����。作為受沖擊的右派家屬�,我不能說受過多少折磨���,我遇見了很多好心人���,我所在的部門,甚至沒人貼過我一張大字報(bào)�。但是這八年在我確實(shí)是難熬的,朋友們贊許我為工作��,更為維護(hù)這個家盡了力��,我�����,只有我��,心頭永遠(yuǎn)感到不安����,歉然,內(nèi)疚���。
我自認(rèn)為是一個在任何條件下都盡責(zé)的編輯�����,一個多少經(jīng)歷過坎坷的妻子����,但我并不是一個好母親。
1997年春
1998年末改定
本文選自《我死過 我幸存 我作證》����,邵燕祥/著,作家出版社��,2016年7月���。
轉(zhuǎn)自《私人史》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|
|
 |Archiver|手機(jī)版|小黑屋|愛鋒貝
( 粵ICP備16041312號-5 )
|Archiver|手機(jī)版|小黑屋|愛鋒貝
( 粵ICP備16041312號-5 )